《國家與認同:一些外省人的觀點》讀記
這本書的編採內容,頗有濫芋充數之嫌。前半本是濫芋,後半本的論述內容才有深度可言。
你以為懂,其實也不一定懂很多的外省人。 國家與認同 總序
「外省人」族群,只有從本省人的角度來看,其定義才是「明確的」。欲跳脫本省人觀點而得到客觀的「外省人」定義,係椽木求魚。
要我來說,那就按照台灣近代經濟史來分。所謂的「本省人」就是國民政府遷台後,失去經濟優勢地位階級的那一群人;他們要鬥爭的階級對象,就是「外省人」。哈哈,雖然我不認同馬克思大部份的經濟理論。但在這種場合,我覺得馬克思經濟學的階級鬥爭論用起來十分方便。
眷村文化
眷村好像一個大家庭。 (p.22)
眷村的形成成為他們獲取生活資源的最佳方式。 相似職業生活下,由眷村媽媽們形成了社區互助的生活環境。因此眷村大家庭類似家族的生活環境。 (p.23)
國民黨政府推行了國軍各級部隊「以軍為家」的運動,透過家這個概念形成軍中彼此的團結,同時也訴求軍中袍澤相互間的緊密關係。 (p.24)
眷村中特殊的「媽媽」稱謂,雖不明其為何如此使用,卻也顯示眷村生活的媽媽們會彼此支援及照顧,好似大家族中的一分子。 (p.25)
《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》,尚道同
村即族。在人口大遷移以及軍隊成員皆來自不同省份之結構下,發展成為一種部落型態的社會組織。與原始部落社會的形成軌跡相近。 關於眷村媽媽的習俗,我依稀記得在其他人類學著作中提過蒙古遊牧部落、北美印弟安部落中,也有相似的習俗。部落男子在外狩獵、作戰,生命朝不保夕。部落中的所有小孩,不分親生關係,皆由所有部落女子共同扶養。對部落小孩而言,扶養過他、餵過他奶的每一位女子,都視同媽媽。
在稱謂上,眷村居民多係獨身或小家庭來台,原有的親屬關係已經消失,便不可能按照輩份關係區分稱謂。是以來台後在眷村重新建構親屬關係的過程中,凡年長於父親與官階高於父親者,皆稱「伯伯」(唸作ㄅㄟ ㄅㄟ);年輕於父親與父親的屬下,皆稱叔叔。而那些伯伯、叔叔的配偶們,由於會互相照顧彼此的子女,為免稱謂上顯得生疏,便冦以家姓互稱為某媽媽。例如隔壁的小石頭(我小時候就是被人這麼叫的),他爸就稱石伯伯,他媽就稱石媽媽。
關於眷村研究,我個人認為從人類學的角度切入,會更有內容可言。
本土意識的塑造問題
對自身「外省人」的身份具有強烈的「原罪感」,他說: 那時候有課堂討論,同學之間會討論,就知道白色恐佈、二二八事件。然後就慢慢會有外省人的原罪感。 (p.62)
所謂「吃台灣米、喝台灣水、卻不會講台語」的說法,似乎在指控他不懂得惜福、感恩、愛台灣,這不僅是藉著語言的使用區辨出身分的差異,更是本質化且同質化地賦予「外省人」這個身分汙名的標籤。 (p.64)
《外省人第二代的國家認同》,孫鴻業
二二八事件中,亦有許多外省籍受害者。為何不見「本省人」的「原罪感」? 白色恐佈的對象,主要也是外省人中的「匪諜」。例如同書《澎湖槍響:山東學生流亡之路》的七一三事件,為何不見討論?我個人認為這種偏差印象的形成原因,至少有: 一、本土意識塑造者選擇性地使用史料。 二、國民黨是執政者,是權力的受鬥爭對象。 三、由於白色恐怖牽涉到許多外省人,國民黨為了避免動搖統治基礎,故選擇掩飾這部份的真相。
「台語=閩南語」。這個等式,突顯了閩南語族群在塑造本土意識運動中的強勢地位,亦有一說為「福佬沙文主義」。這種本位主義甚至排擠了客家語與更本土的原住民族群的地位。因為他們之中,有不少人亦不會說閩南語。
人類學論文,作者自知其生活背景必定會影響其論述的觀點,故通常會在文章中說明作者的背景。
人類學家進行研究工作時,都會預先審視自己是否有先入為主的偏見。由於人類學家的背景、年紀、性別和使用的理論方法,難免都會影響他或她的研究結果或方向,所以這些年來的民族誌研究,人類學家都會在工作報告中列舉說明自己的個人資料。
個人的特質會影響和左右研究的方向和結果。人類學家為了有效處理這個問題,最近都會在他們的學術著作裡,以自傳體的書寫方式一併收錄自己和訊息提供者的背景資料。
《社會人類學:他們的世界》,弘智文化出版,p.51-52
而在這篇社會學論文中,大概是為了符合台灣學術界的「客觀性」(仿自然科學的客觀性),文中完全剔除了作者的背景資訊。但從文中對「台語」一詞的使用方式,我推測作者可能是純眷村子弟或是純閩南子弟,所以對「台語」一詞的使用與論述很粗疏。不像客家語或原住民族群那麼敏感 - 他們不見得認同閩南語族群的「台語」定義。
如果我了解作者的背景,或許能更進一步地分析作者的論述內容在何處偏差了。
台語與閩南語
語言的使用(尤其是台語的使用)成為外省第二代辨識自我和他人最主要的方式。 (p.65)
《外省人第二代的國家認同》,孫鴻業
系上學長對我說:「你是外省人吧?你的名字台語沒辦法唸」。終於了解,被老師點到的福建人、山東人和我這個「其他」,其實都一樣,在別人眼中都是相同的外省人。 (p.113)
《故土與家園》,沈筱綺
是對方不會唸,而非台語不能唸。一個台灣閩南語學者,就知道怎麼唸。不會唸只代表對方的閩南語程度低落。但對方的福佬沙文主義思想,使他不會自省出他的閩南語能力問題。沙文主義真是無知者的最佳保護盔甲。
我的高中國文老師以及大一國文老師,都有鮮明的台灣文學色彩。高中時被彭瑞金教國文(他已自高中退休,現於大學任教);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(今「真理大學」)唸書時的那位國文老師,我已忘記他的名字,只記得他的國文課從頭到尾都在講台灣文學。我記得他們其中一位在上課時提到,唸唐詩時最好是用閩南語。因為唐詩發展年代的官方語言是河洛話。閩南語繼承河洛話古音,所以用閩南語唸唐詩更合聲韻。話是這麼說,但我週遭可以完全用閩南語唸完一首唐詩的人,還真是找不到幾個。試想當某人用閩南語唸一首唐詩時,碰到不會唸的字,我們是該歸咎於「這個字閩南語沒辦法唸」?或是「閩南語不夠熟練,不會唸」?
後記
雖然《國家與認同》這本書大概只有一半的內容有深度,但另一半也是多少有點用處的。它記錄了許多所謂「本省人」的觀點、以及他們貼在「非我族類者」上的標籤。我買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,就是為了預先收集資料,以便將來批駁福佬沙文主義者之用。
本書的副標題雖為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」,但其實大多是「本省人」的觀點。這便是本書論述內容最大的問題所在。作者們在論述時,實際上是站在本土意識塑造者架起的舞台,踩著那些人在台上畫好的腳印起舞。既然跳不出那些人畫好的框架,也就看不到開創性或獨立性的觀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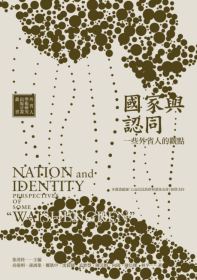
樂多舊回應